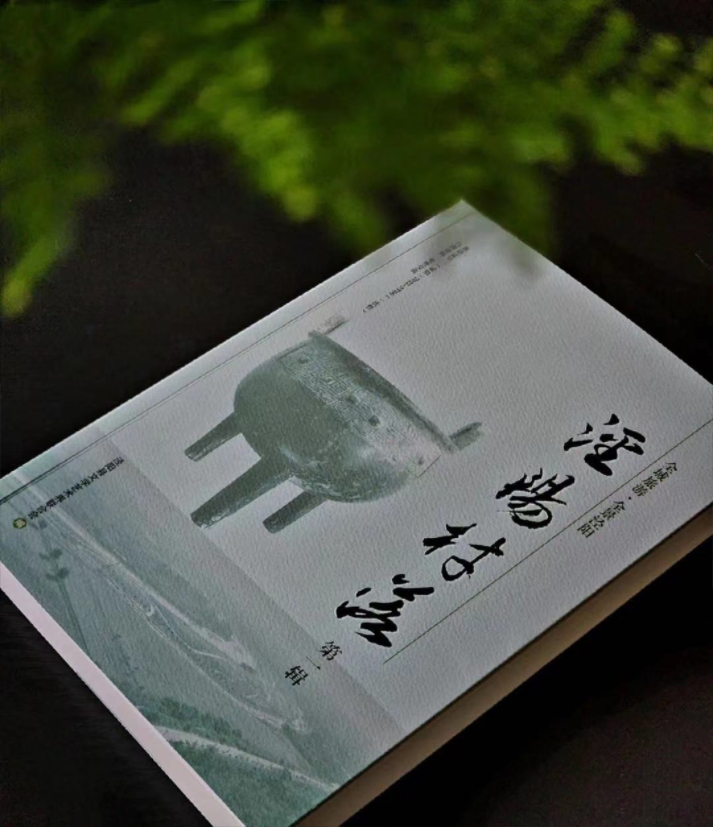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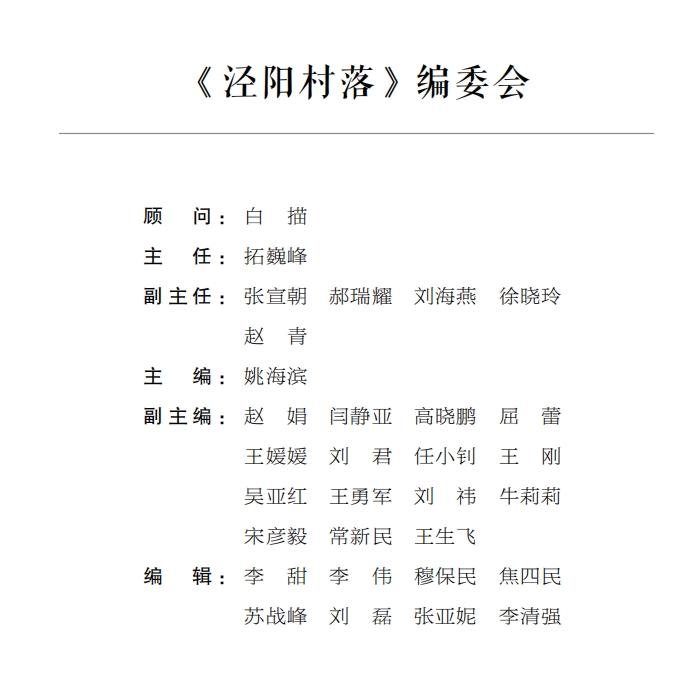
寨里王村的變遷雜記
王淑紅
寨里王村也有人叫半個城��,這是因為村人大都是依涇河北岸而居��,臨崖打窯�,住在窯洞里�。這種叫崖窯�,有別于地坑院的那種地窯。王氏先祖何時來此居住�,已無確切的考證����,涇陽縣地名志載大概在清末光緒后期,但不知何故�、何因、何時來此��。據(jù)老輩人傳說�,這里的王氏族人大概是從北塬上那個王姓祖居地一步步慢慢遷下來的����。解放前,在白王魏家莊子南有我們很多的祖墳��,也有很多地,哪個朝代葬此卻無從考證�。
寨里王以前也是有城墻的,南邊的常被水沖垮���,也就無跡了,北崖上的老城墻至今還有一小塊���,寂寞地在歷史的長河中待著,看慣了涇河的水漲水落�����,也看慣了日出日落�����,更見證了王氏族人的生產(chǎn)���、生活和無奈的遷移。一部分人遷居西北一里半地筑屋而居(據(jù)說當初只是五家人)�,慢慢地人越來越多���,有百十戶人家����,解放后叫西王村���,沿用至今沒變,我的家就在西王。東遷的和郭姓同居���,叫郭王村。從崖窯遷到崖畔上的叫南王����,我小時候還見到幾戶住在窯里的人家�����,戶與戶間距離拉得很長,后來集中規(guī)劃居住���,就都住到一塊了。
我們知道�����,中華民族發(fā)展壯大傳承的歷史,也就是各氏各族的歷史縮影����,不但要重視中華民族的大文化,也不能忘記自己家族的小文化��。這里有我們家族的一個傳說���,也可能是實事�����,也可能是神話����。
鐵扁擔的傳說
涇河是渭河最大的支流,發(fā)源于寧夏六盤山東麓涇源縣境�,它的中上游全部穿行在黃土高原�,下游則流淌在涇渭平原上。它中下游的分界點是北仲山的出山口�����,古稱瓠口�、洪口或谷口�����。谷口向上��,河兩岸山峰對峙����,峽谷綿長�����,石崖高聳,水流湍急���。谷口向下,則地勢低而平緩����,河水如金鐘倒掛,傾勢而下����,一瀉千里���。每遇上中游下大雨,河水暴漲��,涇河則成了脫韁的野馬�,橫沖直撞���,沖毀兩岸的莊稼�����、道路����、村舍���。幾千年來��,兩岸民眾苦不堪言��,深受其害�。

▲寨里王城墻
谷口不遠的北岸�����,土塬畔上依崖挖窯�����,聚居著王姓族人����。村落背靠北塬�����,南臨涇河���,寨里王城墻東西南因勢筑城�����,俗稱寨里王,因城常被水沖毀����,也有人叫半個城。據(jù)傳�����,早在唐代,因有王姓人在鄭白渠上架橋而有王橋(王氏家族祖墳在現(xiàn)在白王鄉(xiāng)魏家莊西南����,并有大片土地,架橋是為了方便祭祖和耕作)�,現(xiàn)有碑文記載,明代中期�,他們就繁衍生息在這兒,世代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
時光不知流淌到那一年����、那一月,城墻�����、村舍�����、莊稼道路也不知被河水沖毀了多次�����,廟宇也建了不少����,有龍王廟、彌勒廟��、菩薩廟�����、娘娘廟���、四王爺廟等,求神拜佛都沒法保護家族的平安�,日子反倒越過越恓惶���。直到有一天�����,有一人大家都稱他老水漂����,因家貧無所度日��,幾輩都在河津渡口做馱工����,也就是從船上向下或向上背馱旅客�����。夏天還好說�����,無非大太陽下曬得多流點汗���,冬天天寒地凍,冷水刺骨��,灘涂泥濘���,結冰腳滑,一不小心就會摔倒�����,摔壞了東西或人,客人就會有意見�����,遇到難說話的人���,非但沒有報酬,還要被罵幾句����,遇到歪人肯定要挨打了�。而這個水上漂的職業(yè)病,就是腳腿濕氣太重����,逐漸地就喪失了知覺,冷熱不自知了�����。
有一族人王敬業(yè)�,是個讀書人��,看到鄉(xiāng)親們受涇河暴水之害�����,就寫了個狀子����,和一群人到四老爺廟玉皇大帝那去告涇河龍王;脾氣暴躁����,率性而為��,禍害沿岸居民��;高居廟堂��,不恤民間疾苦����,枉受群眾香火……如此罪惡共有十條����,高聲念完火焚�����,上達天庭���。這本來也就是讀書人在使性子��,誰也沒當回事�����。誰知當晚�,涇河龍王卻托夢給他并對他說,你好大的膽����,竟敢告我的黑狀��,好啊�����,給你一根鐵扁擔,埋到你村河岸邊���,河岸就會像刀劈斧削一樣,既高又陡�����,水不擾你�����,你也別煩我。涇河龍王說完�,摔門而去。
王敬業(yè)從睡夢中驚醒���,朦朧中向外一望,天黑咕隆咚的����,沒一絲光亮,隱隱能聽到遠處傳來幾聲雞叫���。他披衣起床�����,摸著破城墻�,向村外河邊走去��。正走著����,被啥家什絆了一下�����,伸手一摸���,果真是根鐵扁擔,往起一拿���,沉得很�����,竟然是龍宮特有的玄鐵打鑄的���,烏黑透亮,寒氣逼人�,只覺得一股涼氣直透心窩,人也不由自主打了個冷顫�。他猛地向回跑了幾步�����,覺得不對勁���,停住了腳步慢慢尋思,世上哪有這樣的好事�����,天上更無如此好神����,怕是龍王整治咱吧���。自古民告官���,不是被抓,就是被殺��,哪還有神官為民謀好事的���。想到這����,他悄悄叫起老水漂�,簡單說了事情的經(jīng)過�,叫他趁現(xiàn)在天還沒大亮,找個地方把這個不知是禍是福的鐵扁擔給埋了�����。老水漂抱起鐵扁擔�,順路埋在了村西一里遠的河邊……
從那以后�����,直到現(xiàn)在,船頭狄道渡東�����,寨里王村西大約200米的地方��,北岸河崖高聳�,水浸不透�����,水沖不垮�,水漲不淹���。20世紀的1972年修的備戰(zhàn)橋,本世紀2005年修的關中環(huán)線橋��,都選址在這個地方�����。
現(xiàn)在是“雙龍舞涇河���,二橋鐵擔穿”�。
解放前的印記
我們家族在陜商歷史上也有點薄名的����。我三祖父(也有說是曾祖輩)叫王華亭��,是個生意人����,西北大學李綱教授編的陜商歷史書中有記載��。聽家族人傳說���,他家生意在三原����、涇陽���、王橋���、四川雅安都有,他們家人常住三原鹽店街���,人稱十家院,幾進院子���,抱柱懸對�,牌匾門頂�����,很是氣派����。農村平墳時���,挖出的棺槨套材聽說是梓木楠木一類,日曬雨淋很多年棺蓋都沒爛��,后不知所終�����。民國十八年前后�,陜西三年大旱,赤野千里�,餓殍遍地���,史稱年饉����,我族人先輩便給王姓同族每人發(fā)大洋一塊��,有一郭姓大叔因在我家避荒也發(fā)給了四塊大洋�����。前幾年村中有一位九十歲的老人�����,我叫三叔���,我問過當時一塊大洋能有多大價值,他說能買一畝水地�。試想,如果不是看重家族親情�����,幾百塊大洋是能買幾百畝水地的��。
我們的家族也是有家國情懷���、革命傳統(tǒng)的。我的二伯父王德福�����,1940年守衛(wèi)中條山時犧牲�����,至今尸骨未歸�����,也不知魂喪何處���。我的父親王德明�,又名王尚斌,在三原讀書時��,受我們村附近仁義學校老師���、地下黨員李國棟(禮泉縣舊縣村人,后任永壽縣縣長�����,前多年曾去拜訪過他����,時已九十高齡,居住在政府干休所)影響�,接受了新思想�����,秘密加入了地下黨����。中學畢業(yè)后,因家中經(jīng)濟困頓(我的爺爺和婆都抽大煙�����,三姑二爸都上學)�����,無力再繼續(xù)上學���,也找不到好工作,就聽從李國棟老師的建議�����,去軍隊上做兵運拉隊伍�����,給三原縣池陽鎮(zhèn)頂了壯丁����。我的四伯父王福泰當時是池陽鎮(zhèn)的副鎮(zhèn)長�,是他勸說的����。當時同去的還有同村人王尚虎(我父親叫他四哥����,他們是同學�,也是好兄弟,后來也是我父親介紹他加入了地下黨�。還有一個叫王興和的同村人也是我父親介紹加入地下黨組織的)����。他們參軍的隊伍是陜西省保安旅,曾駐扎過漢中�����、三橋����,因為國民黨的部隊腐敗透頂,長官對士兵非打即罵���,又形勢所迫���,人心渙散,聽說又要調防到外地去�。我父親見拉隊伍的想法很難實現(xiàn)�,就謊稱有病,要去西安看病��,就給連長請假����,由三橋坐火車到西安���,由西安坐火車到三原離開了隊伍�����。禮泉第一次解放時,我父親就隨李國棟在縣政府工作�����,馬家軍攻打禮泉時,就隨禮泉縣政府人員轉移到?jīng)荜栄┖?、魯橋一帶躲避。五月禮泉二次解放后���,就聽從政府安排,到乾縣參加干部培訓學習���,結業(yè)后參加乾縣的征糧工作��,還得過獎章�,后來又安排到長武縣公安局任公安助理員,佩槍就是我們在影視劇中看到的那種駁殼槍(這是我在照片中看到的)����。后來��,長武縣成立了文藝工作團�,我父親小時就愛好玩皮影,也算是和文藝沾了點邊吧���,就有人向領導提議讓我父親去領導劇團�,這樣我父親就當了多年長武文工團的書記����、團長。1975年調回涇陽也是在劇團任領導�。1982年在教育局教研室離休����。王尚虎后來也從國民黨部隊離開參加了新的政府工作,分配到旬邑工作�。和我父親同時參加地下黨的還有王豐崗(后分配在彬縣(現(xiàn)彬州市),任過城關鎮(zhèn)鎮(zhèn)長�、縣工會主席�����,去世后也葬在了當?shù)兀?����。王豐崗介紹加入地下黨的王金福曾當過昭陵一區(qū)仁義區(qū)的鄉(xiāng)長�����、禮泉銀行行長���。
解放后的發(fā)展
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我們村也有多人參加了志愿軍���,他們是王步民、王彥明����、王保亭�、王喜春。至于以后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也是層出不窮。我三伯父的大兒子王永財(又名王新民)就是從西安開關廠參軍的��,后以正營級復員到霸橋熱電廠����,現(xiàn)已去世。
農業(yè)社時代���,西王村在老隊長王庚金的帶領下�,農村集體經(jīng)濟不斷壯大���,蓋有四十八間房,有庫房�、飼養(yǎng)室、開會剝棉花的地方�����。蓋房那一年�����,全村人都沒放假過年����,只因正月初四有兩戶要嫁女兒����,親鄰都要去送親,才放了半天假�����。渠南大水地��,公糧購糧任務很重���,我們一個生產(chǎn)小隊征收的糧比半旱半水的生產(chǎn)大隊的糧都多,分產(chǎn)到戶時��,我們村有戶人家交的糧比西街九隊一個生產(chǎn)小隊交的糧都多���。我們村還是產(chǎn)棉區(qū)����,每家每戶都有交棉花任務,寒冷的夜晚���,坐在飼養(yǎng)室剝棉花����,是個很難受的活��,特別是婦女兒童和老人�。我們生產(chǎn)隊還買過一輛汽車,交糧買化肥比較方便���。那時尿素計劃供應,不好買��,因我二爸王德壽在縣生產(chǎn)資料公司�,村里人也尋他買過氨水����,用車拉回來,倒存在打好的水池子內����,澆地時再放出來����,隨水流進地里��。我們村還在村南人工打的大口井旁種過水稻�,是當時在窯店公社當革委會主任的王文斌引進的�����,不知什么原因�����,種了一季就沒再種。那時人們物質生活普遍都很困頓�,但人與人矛盾較少,快樂很多���,尤其是兒童,個個野得了不得���,偷瓜偷果,上樹摘洋槐花�、榆錢���,下河捉鱉摸魚�����,不吃飯家里都找不到人�。
每個民族����,每個朝代,大有大的英烈�����,小有小的可詠��。他們都是時代的楷模���,歷史的花絮。
最后記錄一點題外話�,20世紀六七十年代毛主席號召學工學農����,開門辦學�����,陜西師范大學就在我們南王村老城墻根辦了一個農場��,叫陜西師大五七農場,每天早上都會聽到他們的廣播:陜西師大五七農場現(xiàn)在開始廣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或現(xiàn)在播放革命歌曲……幾里路外都能聽到�。那時我還很小����,也曾見證過白發(fā)蒼蒼的老教授,褲腿高挽�����,在夏秋的太陽下���,戴著草帽,拿著鐵锨�,晝夜不停地放涇惠渠水淤涇河灘(那時涇惠渠兩岸都是黃土岸,水含沙量很大���,尤其是上游下雨漲水的時候,很適宜淤地)���,使之成可耕之地。大學生坐著廂式大卡車來種收莊稼���,他們把加工好的三角梁拉來��,很快建了好多教室和教職工宿舍。那時狼很多����,我還在一個教授的窯洞(是打在城墻上的)里見到一個被打死的麻灰色的狼,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真狼����。我還見到過學生們開著汽燈,或燃著柴火���,唱著藏族歌曲《北京有個金太陽》�,跳著舞。當時有個姓謝的教授�����,細高個����,夫人瘦小�����,應該是南方人���,老兩口人很和藹,見到小孩去找他們要水喝���,都很親切地給喝水���,沒有討厭農村娃的意思�����。
不記得農場是啥時停辦的。后來涇陽縣劇團娃娃班也在農場原址住過一個時期����。以后形勢變了,五七農場也就留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作者簡介
王淑紅����,涇陽縣王橋人,書法家��,文學愛好者���。
(本文選自涇陽縣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2022年10月編輯出版的《涇陽村落》第一輯)
責任編輯:王順利/《新西部》雜志 · 新西部網(wǎng)

 掃一掃上新西部網(wǎng)
掃一掃上新西部網(wǎng)
 不良信息舉報窗口
不良信息舉報窗口



